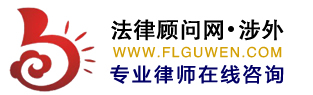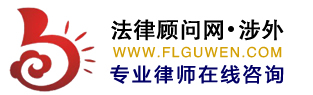因为多年的家庭积怨,李女士竟然在父亲去世多年后才获知其落葬何处,又因为墓碑上没有署自己的名字,李女士不惜将亲生母亲和长兄告上法庭。
近日,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,经过调解,这桩缘起家庭矛盾的“祭奠权”纠纷,终于得到圆满解决。
墓碑上名字漏刻
李女士和长兄李先生早在1999年就已经势成水火。为了拆迁的利益和父母的赡养问题,这对亲兄妹闹得不可开交,双方长期不相往来。特别是从2002年父母动迁购房并与长子李先生共同生活以后,李女士更是难见父母一面。要不是邻居及时告知,2004年3月,李女士甚至还差点错过了父亲的葬礼。
2008年,李女士的儿子从日本留学归国,李女士和母亲的关系稍有缓和,她借机向母亲询问父亲的落葬地点打算自行拜祭,母亲的答复总是含糊其辞。
直到2009年4月,李女士经过多方寻找,才获悉父亲安葬的具体位置。当她去墓园探望时,竟然发现父亲的墓碑上赫然刻着其他三兄妹的名字,独独没有刻自己的名字。
为此,李女士一纸诉状,将母亲和具体负责父亲安葬事务的哥哥李先生告上法庭,讨要自己对父亲的“祭奠权”。
庭上互相推脱
在庭审中,李女士气愤地表示,这肯定是长兄李先生因为宿怨,利用母亲不识字,故意把李女士一家的名字漏掉。这样的行为侵犯了自己对父亲的祭奠怀念之权,应当受到法律的惩戒。为此,李女士和丈夫要求对方全额承担费用,将自己一家三口的姓名补刻上父亲的墓碑,出具《悔过书》,当庭向自己赔礼道歉,并向李先生索要精神赔偿金1元。
长兄李先生则提出,妹妹李女士与其他的兄弟姐妹及母亲关系不睦,长期不来往。当初购买父亲墓地、墓碑的是母亲,自己只是作为母亲的代理人办理了相关手续。至于墓碑上的子女署名问题,因为当时母亲没有授意自己将妹妹的名字列入,所以自己既没有责任、也没有义务擅自将其名字刻上墓碑。况且,考虑到当时妹妹和家人的矛盾难以调和,如果擅自将她名字刻上墓碑,反倒有可能激怒她,这也是当时他没有将李女士一家人的姓名刻上墓碑的原因。
李母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到庭,她的代理人表示,李母年纪大又不识字,墓碑的置办都是由儿子做主,李母对于当初墓碑上的刻字问题未曾有过表态,也不是很了解。
庭后调解名字补刻
庭审结束后,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。
承办此案的陆敏法官认为,墓碑不单是标记故人安葬地的标志,也是承载着亲属哀思的特殊物。一方面,对于死者,按照我国民间传统,墓碑上的文字是其一生的总结,碑上镌刻的亲属名是一种公示,表明了其血脉的延续,死者的墓碑上缺少女儿的名字,这是对死者的不敬。另一方面,墓碑是亲属寄托哀思、祭拜扫墓的重要物品,李女士作为死者的女儿,有权对死者进行祭奠,因此李先生的做法侵犯了李女士对父亲的祭奠权。
法官通过以上两点对当事人进行了劝说,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,由李先生协助李女士办理墓碑补刻事宜,费用由其母亲代为承担。
|
|
|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|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父母的墓碑上缺少子女的名字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“祭”是孝的延伸,我国自古就有“生则养,没则丧,丧毕则祭”的习惯。子女把父母赡养送终后,在清明、冬至时节,全家济济一堂,坟前插上香烛,摆上供品,祭奠父母的音容笑貌,祈求先人保佑子孙。这是每个普通家庭例行的祭奠,也是子女对父母尽上的最后一份孝心。虽然现在社会发展越来越快,但是这样延续千年的祭奠活动并没有因为时代的不同而逐渐衰退。
“祭”同时也是对死者生前的肯定。墓地的选置要彰显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;墓碑上的铭文是对其一生的赞扬和总结;附刻的子女姓名牵系着血脉相承的亲情;如此,再得到后辈年年供奉。通常人们认为这样才是“善始善终”的完美一生。
祭奠作为一种风俗习惯,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据非常独特的地位。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,子女对父母有死葬的义务,但是根据立法精神以及社会的道德伦理,子女应为父母养老送终。同时,祭奠作为一种“礼”和“孝”的外延,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范畴的概念。
因此,由“祭”引起的纠纷,用道德伦理来劝服争议双方,以公序良俗的惯例来调处纠纷,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。本案中,法官从“对死者敬、让生者孝”两个道德层面对双方进行了耐心疏导,使当事人从情感上更容易接受,这番调解远比“硬判”的效果好。
|
|
|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|
李家的这起家庭矛盾虽然在法官的调解下,得到了圆满解决,但它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:“悼念权”或者称为“祭奠权”。那么“祭奠权”是不是一种民事权利呢?就此,记者采访了审理本案的法官。
法官对记者说,祭奠,简单地说,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(通常是去世的亲人)表示悼念和敬意的一种情感活动。作为一种风俗习惯,祭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据非常独特的地位。它关涉到传统礼法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——孝。根据《礼记·祭统》,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——“孝子之事亲也,有三道焉:生则养,没则丧,丧毕则祭。养则观其顺也,丧则观其哀也,祭则观其敬而时也。尽此三道者,孝子之行也。”而孝不仅局限于道德教化的范畴,同时它还被写进封建社会的法典之中,以国家强制力的形式予以保护。如汉代立法曾明确规定,父母死,守丧三年。由此可见,祭奠表面上看是一种风俗习惯,其背后是中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礼法传统和恪守孝道的家族伦理。礼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中体现,融道德、宗教、法律等为一体,蕴含着多重属性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祭奠作为社会规范的礼,从一开始就具有法律的属性。
法官告诉记者,从法律性质上看,祭奠权应属于公民身份权的范畴。所谓身份权,是民事主体基于某种特定的身份而享有的民事权利。而祭奠权是民事主体基于亲属关系而产生的一种祭奠的权利。再进一步说,所谓的祭奠权,就是每一个近亲属,对已故的近亲属(尤其是尊亲属)都有祭奠的权利,近亲属之间应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,相互通知,相互协助,不得干涉、阻挠。
法官说,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祭奠权,但我国现行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,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。根据该条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以及民法中公序良俗的原则,可以推定子女不但对父母拥有生养责任,同时也有死葬的义务。根据权利、义务相统一的原则,该法律义务的背后隐含着一项法律权利,即子女有资格对抗或者请求他人相应地为或不为一定行为,以完成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作为。至于祭奠活动则是死葬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,从时间上看,应贯穿于父母去世时与去世后。
本案中,原告李女士因动迁矛盾,与其他家庭成员交恶,长期不相往来,导致李父去世后,母亲和兄长没有告知其父亲的落葬地,更没有在墓碑上刻上李女士的名字,致使李女士无法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表达对父亲的哀思。
对此,法官说,无论出于何种原因,这些做法均表明死者及其亲属对此人的否定性评价,且这种评价是长久、持续的,起到某种程度的“公示”效应,会给李女士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,因此李女士的祭奠权的确受到了侵害,且具有一定的精神伤害。 | |